

来源:慧泽医药 2025-10-20 浏览量:221
近期,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的《化学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质量风险评估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在业内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有人称之为“BE刑法典”。这个比喻,形象地道出了这份文件的分量。它绝非一次简单的技术补丁,而是标志着中国仿制药研发与评价体系的一次根本性转向——从过去对“统计结果是否达标”的单一关注,全面升级为对“研究全链条质量体系是否合规”的系统性审视。
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社会上关于“血压不降、麻药不睡、泻药不泻”的热议,以及长期以来“仿制药不如原研药”的普遍认知。作为一名亲历了中国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全过程的科研工作者和创业者,我认为,这份指导原则的出台,正是监管层对上述社会关切的最有力回应。它试图从根源上铲除导致“信任赤字”的土壤,为我们行业正名,为患者信心筑基。今天,我想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份文件背后的深意、行业当前的痛点以及未来的破局之路。
在深入解读新规之前,我们必须正视问题的根源。公众乃至部分医务工作者对仿制药的疑虑,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首先,是历史遗留的“认知惯性”。 在我国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仿制药研发的出发点是解决“有和无”的问题,目标是达到原研药的质量标准,而非强调疗效的一致性。那个时期,“老百姓吃仿制药,有钱人吃大厂药,领导干部吃进口药”的说法广为流传,这种对仿制药疗效差的固有认知,至今仍在影响着许多人的判断。
其次,是科学与科普之间的“信息鸿沟”。 2016年之后,我们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我国的评价标准,无论是在制剂杂质控制等质量标准上,还是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的生物等效性(BE)评价方法和标准上,都已基本与国际接轨,甚至在部分环节要求更高。这套基于药物动力学的BE评价方法,通过比较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健康受试者或患者体内的吸收速度和程度,是国际公认的科学评价疗效一致性的“金标准”。然而,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我们针对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公众的科普培训严重缺失。研发者洞若观火,而实际的处方者和使用者却雾里看花,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仿制药有效性不被认可的重要原因。
再者,是“价格与价值”的传统思维悖论。国家药品集采政策极大地降低了药价,惠及了民生,但几分钱一片的降压药、几毛钱一片的抗感染药,也冲击着公众“一分钱一分货”的传统认知。当药品价格严重偏离其在大众心中的“临床价值”时,怀疑其质量便成为一种本能反应。这背后也折射出我们医保基金“广覆盖、保基本”定位下,对高端药品市场与差异化需求的覆盖不足,导致了“好药无处卖,好药无处买”的暂时性困境。
最后,也是最为核心的,是行业内部存在的“技术与管理”短板。 这正是本次指导原则重点打击的领域。部分BE研究确实存在质量隐患,可能导致“一次性评价”现象。即申报时精心准备的样品和工艺,在获批后的商业化生产中,可能因辅料来源、工艺参数微调、生产场地变更等未能严格保持与原研药的一致性,导致实际市售产品的疗效出现波动。此外,虽然监管严厉打击,但仍不能完全排除极少数研究中存在的弄虚作假行为,这些个案经过放大,足以摧毁整个行业的信誉。
本次《指导原则》的出台,可以说是“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仅是一份技术清单,更是一种监管哲学的宣告。我认为,其核心思想体现在三大深层变革上:
变革一:从“唯结果论”到“全过程质量管理”
过去,审评的重点很大程度上落在最终的统计分析结果是否落在80%-125%的区间内。现在,监管的探照灯照亮了BE研究的每一个角落。文件系统地列出了从“研究条件”、“试验设计”、“临床实施”、“生物分析”到“数据统计”全流程中可能存在的上百个风险点。
例如,在试验设计环节,文件明确指出受试者例数不足、清洗期设置不当、采血点设计不合理(如Tmax附近点稀疏、采血时长不足)等,都可能直接导致研究失败。这要求申办方必须基于充分的文献调研和预试验结果,进行科学、严谨的设计,而非凭经验“拍脑袋”。
在临床实施环节,文件对受试者管理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防止受试者短时间内重复入组、杜绝利益相关者参与试验、加强受试者依从性管理以避免事后剔除……这些条款直指以往临床操作中的灰色地带。它强调,一个高质量的BE研究,必须是“管出来”的,而不是“测出来”的。
变革二:从“数据真实性”到“体系可靠性”
数据真实是最低要求,体系可靠是更高标准。新规强调,质量必须是“源于设计”(QbD),并贯穿于始终。这意味着:
风险识别必须前置:在研究启动前,就必须系统性地识别所有潜在风险,并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
过程控制必须盲态:在生物分析和数据统计环节设置信息屏障,防止主观预期干扰客观数据,是保障研究科学性的“生命线”。
决策链条必须透明:任何数据的剔除、分析方法的变更,都必须有预先设定的、科学合理的标准,并在研究报告中完整记录和论证。文件特别指出,基于统计分析结果或单纯的药代动力学理由事后剔除数据,将导致研究结果不被接受。
这实质上是在引导企业构建一个自我发现、自我修正、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体系。监管核查的将不再仅仅是那一摞摞报告和图谱,更是支撑这些数据产生的整个体系是否健全、有效。
变革三:从“申办方主责”到“各方责任共担”
文件第54-59条特别强调,当申办方将工作委托给CRO时,必须谨慎评估CRO的风险识别与管控能力,并有责任和义务对其进行监督。这彻底改变了过去部分申办方“一委了之”、“CRO背锅”的心态。未来,选择一家具备科学理念、技术实力和健全质量体系的CRO,将成为申办方立项决策的关键一环。这必将推动CRO行业加速洗牌,促使真正有技术、有管理的优质服务商脱颖而出,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健康生态。
面对如此严峻的监管态势,行业参与者不应仅仅视其为“紧箍咒”,更应将其看作是一次“分水岭”,是构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历史性机遇。我认为,破局需从以下几个层面系统着手:
1. 回归药学本源,夯实物质基础
我始终坚信,BE的核心在药学。如果制剂本身没有做到与原研药的高度一致,再完美的临床试验设计和管理也无法“无中生有”。新规在“试验设计”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良好的处方工艺及临床前药学研究验证是仿制药与参比制剂生物等效的物质基础。”
因此,药企必须:
深度逆向工程:不仅仅是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深入理解原研药处方设计的逻辑和关键工艺参数的控制依据。
强化体外研究:满足于几条法定溶出曲线相似因子(f2)达标是远远不够的。应致力于建立具有高区分力的、能反映体内吸收特征的体外溶出方法,即构建体内外相关性(IVIVC)。这将极大地帮助制剂处方的优化和筛选,降低BE失败的风险,并为上市后的变更提供科学依据。
2. 构建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实现“风险可知、可控、可接受”
新规的灵魂在于“风险”二字。药企和CRO需要将GCP、GLP等规范要求,内化为一套可执行、可追溯、可审计的标准化操作流程(SOP)。这包括:
事前风险评估:在项目启动前,组织临床、药学、生物分析、统计等多部门专家进行联合评审,识别潜在风险点。
事中严格管控:在受试者筛选、给药、样本采集、储存、运输、分析等每一个环节,设立关键质量控制点,确保操作零偏差。
事后完整溯源:确保从一份生物样本到最终统计报表的每一个数据,都能被清晰、完整地追溯,所有方案偏离和异常情况都有据可查、有因可循。
3. 拥抱技术创新,驱动评价升级
在“体系合规”的同质化竞争下,技术将成为下一个决胜点。
IVIVC技术的深化应用:不仅仅是作为研发工具,未来更可能成为监管和质控的工具。通过建立个性化的、体内外相关的溶出方法,可以为上市后产品的质量一致性提供更灵敏的监控手段,防止“一次性评价”。
模型引导的药物研发(MBDD):利用生理药动学(PBPK)模型等工具,模拟药物在体内的过程,可以优化试验设计,提高成功率。
数据管理与统计的智能化:利用先进的数据管理系统确保盲态、防止篡改,并采用透明、可重现的统计代码进行分析。
展望未来,中国的仿制药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蜕变。
首先,监管与行业将共筑“信任”基石。 通过更严格的现场核查、数据透明化要求、以及对“整体证据”的综合评估(如要求申报方提交既往失败研究的根本原因分析),监管机构将引导行业走向更科学、更诚实的发展道路。单纯依靠“概率”或“技巧”通过BE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其次,行业整合与分工将加速。 缺乏技术积累和质量体系薄弱的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而具备科学理念、技术纵深和体系能力的头部药企和CRO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行业分工将更加细化,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将成为共识。
最后,我们的目标不应止步于“通过”BE。 真正的成功,是让每一片上市的仿制药,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都能持续稳定地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疗效和安全性。这需要我们建立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思维,将BE研究的精神贯穿于从研发、生产到上市后变更的每一个环节。
《化学仿制药生物等效性研究质量风险评估指导原则》的推出,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既是一场大考,也是一次涅槃重生的机遇。它逼迫我们离开曾经的舒适区,回归药物研发的科学本质与严谨精神。破局“仿制药不如原研药”的困境,没有捷径可走。它需要我们行业内的每一位参与者——药企、CRO、研究者、监管机构——共同努力,用最扎实的药学研究、最严谨的临床试验、最透明的数据管理和最健全的质量体系,一点一滴地重新赢得医生和患者的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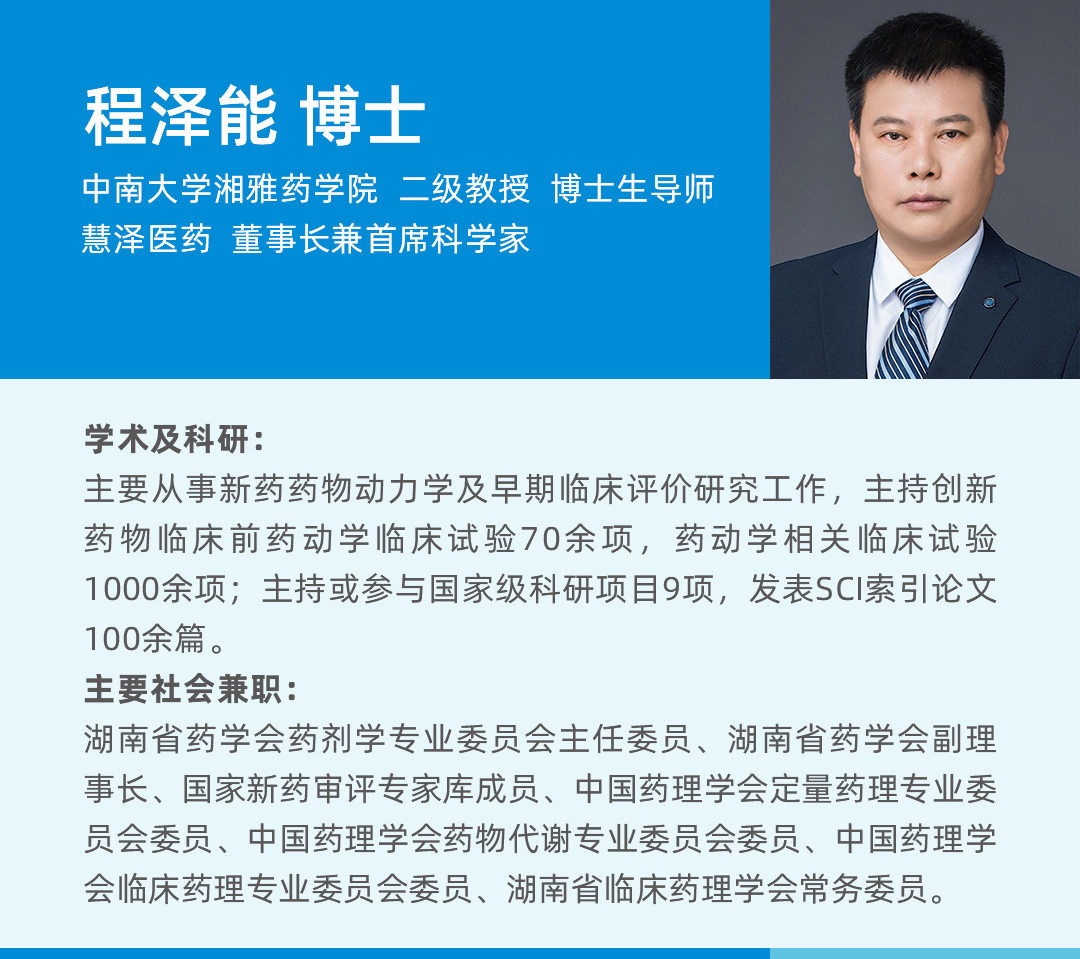
文章部分内容出自:杏林泛舟 MedSeek(本文主编|Herak 责编|Max)
杏林泛舟平台深耕临床研究生态,汇聚药企、机构、服务商与专家资源,致力于打造透明、高效、可信赖的专业内容平台。欢迎关注「杏林泛舟 MedSeek」公众号 / 视频号】,获取更多专业内容~
上一篇:暂无数据